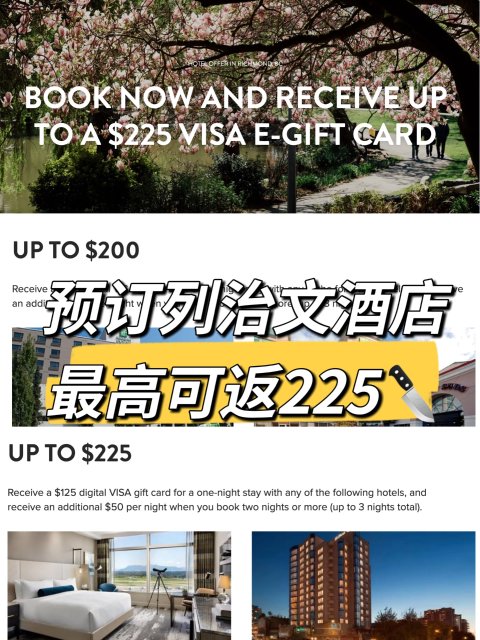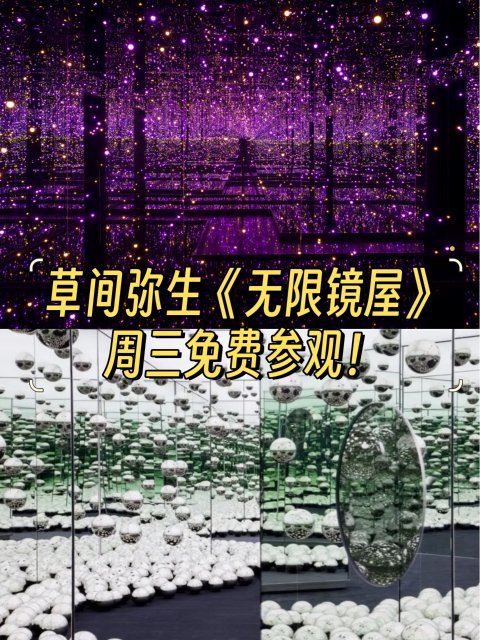2022年,我在一家食品生产公司担任物流经理。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当时她们分别七岁和四岁。作为单亲妈妈,我把闲暇时间都用在跳舞、阅读以及与朋友们相聚。
九月份,我感到胸部右侧不时地疼痛。我没有家庭医生——六年前我加入了省级的等候名单“Health Care Connect”,但一直没有好消息——所以我开始在网上查找我的症状。除了疼痛外,我并没有乳腺癌的典型症状,如皮肤红肿、凹陷或肿块。但对于黑人女性来说,红肿并不常见。我以为可能是乳腺管感染,但没想到是癌症。
大约两周后,我去了当地的临时诊所检查。尽管我在诊所上午9点开门前15分钟就到了,但已经有很多人在前面,工作人员让我回家。之后的几天,我又去了几次,或是一开门就打电话,但我从未看到医生。
三周后,我放弃了,直接去了阿贾克斯-皮克林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疼痛已经变得持续且我摸到了一个肿块。我等了八小时才见到医生并进行了扫描。医院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做活检;扫描显示我右乳有一个大肿块。
接到结果的电话时,我正在家中。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侵袭性乳腺癌——浸润性导管癌。它已是四期,且已扩散至肺部。我哭了一会儿,但很快调整了情绪,集中精力想着如何继续前行。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接受了13轮化疗和免疫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化疗真的很糟糕。我经历了严重的关节痛、疲劳和思维模糊,还掉了头发。我在2023年7月完成了化疗,但仍在接受免疫治疗——副作用包括关节僵硬、关节痛和疲劳——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我的状况被认为是稳定的:肿瘤没有增长,但也没有缩小。
我生病时的房租每月2000加币,加上汽车分期付款——这些是我工作时能承受的,但失去收入后就不行了。我几乎因为拖欠房租而被驱逐。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被诊断出癌症后发起了一次GoFundMe活动,筹得了大约27,000加币。一段时间内,这笔钱帮助我支付了包括OHIP未覆盖的医疗费用在内的账单。我靠积蓄生活,直到今年八月终于获得了残疾福利。

我仍在为我和我的女儿们寻找家庭医生。我的癌症很凶猛,但我认为有了医生,我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本可以在一期甚至更早时就被诊断出来。如果我有医生支持,处理我的治疗也会容易得多。黑人女性的乳腺组织通常比白人女性密集,这是我们更容易患乳腺癌的因素之一。如果我有医生,我可能能定期进行乳房X光检查。
我想专注于与癌症共存,而不是可能死于癌症的可能性。我的女儿们知道我患有癌症,但她们还太小,无法理解我的病情有多严重。我教她们相信更高的力量。我要求医生们不要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他们说我在未来五年内仍然存活的机率只有26%,但他们不是上帝。
文章来自:TorontoLife,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