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Cait Alexander在Leaside家中被伴侣殴打,濒临死亡。尽管证据确凿,该案件却从未进入审判程序,原因很简单:耗时太久。一个超负荷的司法系统如何让受害者蒙受失败。

*以下故事以女主第一视角去讲述(文中“我” 代表Cait Alexander)
遇到“真爱”
2020年11月21日,我第一次遇见了我的前任,我们称他为Carl。
那是新一轮新冠封锁的前夜。我的一位闺蜜和我在约克维尔的Kasa Moto餐厅共进晚餐,把它当作一切关闭前的“最后的晚餐”。在餐厅,我们遇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之后受邀去了Carl的家。
当我们到达时,我被介绍给了Carl,但我们没聊太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他的迷你金毛贵宾犬玩。一周后,Carl发短信给我,说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我的号码。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开始频繁地短信聊天。他发给我狗狗的照片,问我何时能再见面,但那时我正忙于假期。直到一月中旬,我们才见面。
他邀请我去他家,和另一对夫妇一起共进晚餐。他开车来接我,这让我觉得他很绅士。那晚我们过得很愉快。第二天,我必须离开城镇。我是一名演员,当时正在魁北克拍电影。
我不在时,我们持续通过短信交流,慢慢了解彼此。Carl当时40出头,似乎很稳定且经济上很宽裕。他事业有成,拥有一栋位于Leaside的漂亮房子,有五个卧室和后院游泳池。而我的事业也正起步。在疫情期间,我接拍了Hallmark和Lifetime电影,还出演了亚马逊剧集《黑袍纠察队》。2020年,我的祖母去世后,我继承了一笔遗产,所以我也感觉经济上很稳定。
我告诉Carl关于我的工作、家人以及我对全口味薯片的喜爱。他则谈起他10岁儿子(我们称他为Nicholas),是他之前一段关系中的孩子。拍摄期间,我回到多伦多时,他接我并带了我最喜欢的薯片,这让我印象深刻。几天后我需要返回魁北克完成拍摄,Carl提议开车送我。途中,我们在他上大学的渥太华停留,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朋友们。
一周后回到多伦多,我们正式确定了关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几乎都住在Carl家里。我认识了他和前任的儿子Nicholas,我们相处得很好,一起玩Uno牌、复活节时藏彩蛋。我还带他去King Township的牧场学打马球,他成了我的小伙伴,甚至叫我“第二个妈妈”,我很喜欢这种感觉。Carl给我花,告诉我我们会成为一个家庭。我也承担起传统家庭角色,做饭、布置房子和设计花园。每晚我们一起吃晚餐,之后看《Wheel of Fortune》或《Jeopardy!》。
我们经常一起去森林里远足。交往一个月后,Carl开始谈论健康生活,想把地下室的一间卧室改成健身房。他提议我们戒酒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毕竟疫情期间大家都喝了不少酒,于是我们决定一起戒酒。他对我说,我现在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很喜欢听到这句话。他还给了我一张信用卡用于家里的开销。
我的家人也立刻喜欢上了Carl。我的父母来看我们时,看到他是个好父亲,也很照顾我。我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住在多伦多,开始经常带着女朋友过来和我们一起玩。Carl还贴心地给住在BC的另一个兄弟寄小礼物,比如大麻。
四个月后,我放弃了公寓的租约,把剩下的东西搬进了Carl家。一切发展得太快,加上持续的封锁,让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一起。这并不是坏事。我们相爱了,甚至开始谈论结婚。我对新生活充满期待,感到非常幸福,且坚信美好的时光永远不会结束。
绅士男友竟是“瘾君子”
2021年5月,我30岁了。决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为一些朋友举办小型晚宴。我们请来了私人厨师。自从2月以来我们一直戒酒,所以Carl问我是否想喝酒。因为是我的生日,我破例了,我们一起喝了口龙舌兰。
就在庆祝活动中,一个陌生人走进了房子。Carl介绍他是私人教练,但很快就显露出他是个毒贩。Carl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们需要可卡因,我很震惊。我不吸毒,也没有要求。面对他的反应,我觉得没有选择只能接受。我们一直熬到凌晨2点,然后大家才回家。
我希望这只是一次性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天后,Carl下午带着狗去散步,回来后开始说他需要可卡因。他打电话给同一个毒贩,毒贩带来了更多。Carl吸了几口后告诉我他想发生性关系。他说,如果我不和他一起吸可卡因,就说明我不爱他,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会找另一个愿意的女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看到他这副模样让我很困惑,但我只是想取悦我的伴侣。我以为我们相爱,想让他开心,但我也很害怕。
禽兽漏出獠牙
随着夏天的临近,我们开始邀请别人来家里烧烤和开泳池派对。2021 年 5 月 29 日,Carl第一次对我们施暴。当时我们正和一些朋友和邻居小聚。大家一起聚会喝酒。包括Carl在内的一些人吸食了蘑菇。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他发怒的原因,但他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失去了控制。他把我们的一把户外餐椅扔过栅栏,扔进了邻居家的院子里,然后他踢了狗,把一个巨大的陶罐砸在了泳池甲板上。所有人都震惊了。派对上的一些客人试图阻止他,但他们也无能为力--Carl身高 6 英尺 3,体重 230 磅。他不停地说:"这他妈是我家!” 我开始收拾玻璃,我弯下腰的时候,他想踢我。幸好,我在掉进碎玻璃之前抓住了自己。这促使派对上的人和Carl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我需要离开,于是去了邻居家,开始嚎啕大哭,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是什么激怒了Carl。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零发飙。几个小时后,当我回到家时,Carl已经怒不可遏。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和邻居一起住?你不是一个真好的女朋友。”
我为什么不离开?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有一个支持我的家庭。但那天,我内心的某些东西破碎了
第二天,当Carl清醒过来时,他向我道歉,说自己不敢相信做了那些事,但他也怪我,说我没有做好让他冷静下来的工作。他提议我们回归清醒的生活方式,还建议我们单独去度个周末。因为疫情,旅游选择有限,我找到了位于魁北克切尔西的一个水疗中心,并预定了6月初的周末。
前两晚还不错,我们在水疗中心度过了愉快时光。但在我们该回多伦多的前一晚,Carl决定去渥太华的老兄弟会房子,他带着一箱箱啤酒,我能看出他很享受这种英雄式的感觉。他告诉那些年轻的兄弟会成员,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也能像我一样,拥有成功和女人。
当我们准备回切尔西的酒店时,Carl已经喝醉了,所以我得开车。起初,他不愿意把车钥匙给我,直到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我说得对。整个回程中,Carl情绪暴力,骂我“贱女”“荡妇”。我告诉他应该停止喝酒,想好好享受我们的假期。反驳他让他暴怒。到我们停车时,Carl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猛撞在驾驶座窗户上。那是我第一次被这样对待,我愣住了,感觉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我心想:好了,我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一刻,我看到了Carl的真实面目,我知道以后得格外小心。
为什么我没有离开?我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有资源和支持我的家人。我知道他的行为是错的。但是,当你爱一个人时,一切都会改变,你会忽略明显的问题。我不想以疫情为借口,但当时的世界如此封闭,感觉Carl和Nicholas是我唯一的依靠。之前的一切都很好,我以为我们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回到酒店,躺在床上看《美国贪婪》。我很痛,但我们从未讨论过。那一天,我内心有了裂痕。身体上,我无法与Carl抗衡,他让我感到他掌控了一切。我开始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脱离联系,只专注于不再犯错。
就在这个时候,新闻报道开始报道所谓的 “Jordan判决 ”的影响。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但它正在成为法庭上的一场危机。这要追溯到 2016 年,一起名为 R. 诉 Jordan 的案件。一位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素里市的名叫巴雷特-理查德-乔丹(Barrett Richard Jordan)的年轻人因贩毒面临刑事指控,但由于拖延,他的案件花了近 50 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审理,在此期间,他一直处于限制性保释令之下。他的律师将他的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认为拖延是违宪的,最终他胜诉了。因此,加拿大省级法院直接审理的刑事案件应在 18 个月内结案,而需要审前调查或由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则不应超过 30 个月,否则可中止指控。乔丹案旨在保护被告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但在负担过重的司法系统中,这也意味着,无论针对他们的证据多么有力,罪犯都可以在法院从未裁定其是否有罪的情况下一走了之。
在乔丹案判决后的第一年,加拿大有 200 多起案件因延误而被驳回。到 2019 年,近 800 起案件被暂缓审理,其中包括对儿童的性侵犯、谋杀和亲密伴侣暴力等罪行。从2020年起,安省的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因撤销、中止、驳回或解除指控而告终。在此之前的七年里,大多数案件都有了判决,其中大部分是有罪判决。
那年夏天,Carl 经常喝酒,主要是伏特加。有一天,他下午五点醉醺醺地回到家。他咆哮着说我和Nicholas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我们俩总是在一起,然后他拿起一个餐盘扔向Nicholas。幸好Nicholas躲开了,盘子砸在了他身后的墙上。Carl随后试图离开。他用推土机冲进了车库,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我不能让他开车,因为我知道附近有很多孩子。于是我挡在他和车之间。他一把抓住我,然后猛地关上车门。我的身体左侧从肩膀到臀部留下了一块淤青,但至少我赢得了这场争吵,他也没有在这种状态下开车出去。
Nicholas告诉我,当他爸爸喝酒时,他感到不安全,也不想在我不在的时候来家里。他察觉到我和Carl之间有问题,并说如果我离开Carl,他也会离开。自从我开始与Nicholas花更多时间以来,我和他的妈妈关系很好。她经常发短信说Nicholas很喜欢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并感谢我在他身边。一次,他对我说:“妈妈说如果爸爸有任何问题,你可以住我们家。”
事情继续恶化。我健康状况变差,因为我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我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掉了15磅,降到110磅,几乎没有睡觉。7月中,我在电影《最幸运的女孩》的拍摄现场做夜间临时演员。大约凌晨3点,我收到了家门前摄像头的通知,看见几位我不认识的女性进了屋。我开始恐慌,认为Carl把她们带回家发生性关系,我不停地颤抖,发生了严重的恐慌发作。现场有人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我被送到了多伦多西医院。我的生命体征正常,但医生看出我有问题,他问:“家里发生了什么?”我立刻泪如雨下。
医生劝我找社工谈谈,但我没有。我感到非常羞愧。我拼命抓住对Carl 的第一印象不放,我非常想拥有他和Nicholas提供的家庭,想让一切回到最初的样子。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感受到了爱和安全。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就好像我的大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所以我对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我的朋友、父母和兄弟。
不确定的日常工作仍在继续。下班回家后,我不知道Carl会是什么状态。恐惧和不安持续不断。我会想:他喝酒了吗?他出去了吗?他要去哪里?在这之间,我们尽力表现得像个正常的家庭。我们去玩卡丁车,参加Nicholas的五年级毕业典礼,还计划去大狼山庄旅行。在这期间,Carl的表现时而体贴周到,时而粗暴无常。有些时候,他会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他有多爱我。有时,他会拿着我一个昂贵的手提包靠近煤气灶的火焰,威胁要烧掉它,以此来嘲弄我。
七月的一天,我们在争吵,我都不记得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前厅走廊里,他把我的脸狠狠地撞到了前厅的大木门上,把我的前额撞开了。我离开后去了父母家。当他们看到我的伤时,我撒谎说我绊倒了,撞到了头。我父母一看就知道出事了。妈妈说我应该搬出去住,但我舍不得离开Nicholas。我真的很爱那个孩子,我仍然不愿相信我们之前的完美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年夏天,我在巴里拍摄了几个通宵。其中一次拍摄结束后,我在早上 8 点左右回到家,开门时Carl就在门前。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对劲。他一夜没睡。他把一袋可卡因塞到我手里,说:"我要你把这个拿走。把它冲掉” 我感到很沮丧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还得照看一个大男人。于是我冲了可卡因,上床睡觉了。我在下午一点左右醒来,Carl还在生气。也许他买了更多的可卡因,或者发现了他藏起来的毒品。我给他做了午饭。然后他说,“我需要更多的酒。我的车钥匙呢?”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反正开车也不是个好主意。
他似乎以为我把他的车钥匙藏起来了,这更激怒了他。他抓起我的香奈儿包,点燃炉子,把包悬在火上。他一直坚持说我藏了他的车钥匙。然后我生气了 “我他妈再也受不了了”,我对他说。“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不知道你的车钥匙在哪儿”
我上楼进了卧室想找个地方收拾行李,但他追了过来我从没见过他这样,他抓住我,开始打我。他把我的头狠狠地撞到了一个门洞上,把我的头劈开了--右边一条完美的线。我大声叫他住手。但我意识到,反抗只会让情况更糟。面对这么大的人,我根本无法自卫。
他开始像扔布娃娃一样把我扔来扔去,拖着我在硬木地板上走来走去。脊柱对地板的压力导致我背部的部分皮肤脱落。他趴在我身上,按住我,对我拳打脚踢。然后他站起来踢我。他的脚趾甲钻进了我的皮肤,划破了我的肋骨。我全身上下无一幸免。我的鼻子裂开了。我本能地用左臂做盾牌,左臂上全是血和瘀伤。
我不知道那场殴打持续了多久。大概有半个小时吧。Carl离开房间,回到楼下。我找不到手机打电话求助。我拿起 MacBook,打开 Photo Booth,尽我所能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我自己、伤口和瘀伤,还有满屋子的血。我能听到他回到楼上的声音,于是我迅速给我名单上的第一个联系人发了一条两个字的 WhatsApp 消息。那是一个叫Jonathan的导演朋友。信息是一个拼写错误的 “plese help”。他没有任何上下文,但他回复了,我永远感激他。Jonathan试着给我打电话,但因为找不到我的手机,我也没接。于是他联系了我的经纪人,他们在我的朋友和家人中展开了搜索。
与此同时,Carl拿着一根木制擀面杖回到房间。他开始用擀面杖攻击我,打我的后背和胳膊,而我则试图自卫。他按住我,再次压在我身上,试图用拇指挖出我的眼睛,手指按进我的后脑勺。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说,“我的钥匙呢?” 他就是找不到他的车钥匙。
20 多分钟后,Carl又下楼去了。于是我拿起笔记本电脑,尽可能小声地开始给房间拍照。床上和地板上都是血。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万一我没能活着出来,我想至少我的笔记本电脑上会有发生过什么事的证据。我不敢下楼。不知为什么,我想,如果我能把自己洗干净,也许他就会冷静下来。于是我进了浴室。这是最恐怖的经历,我看到鲜血从我的身体里涌出,和水混合在一起,流过大理石淋浴地板。我能感觉到头上和耳后的伤口。我头发上的血怎么也洗不掉--血浆和头发的多孔性是有关系的。我只想洗干净。我记得我当时非常沮丧和愤怒,因为我洗不干净。
洗完澡后,我穿上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粉红色的家居服。我以为Carl不会再伤害我了,但他没有。他回到卧室,又开始了新的动作。我的意识时好时坏。我不知道第三次殴打持续了多久。但有一次,他带着狗出去散步。
当我的经纪人在三个多小时内无法通过电话找到我时,他们最终报了警。当天傍晚,警察出现在我们家门口。虽然Carl不在,但他可以通过环形摄像头看到警察就在门外。这时,我找到了我的手机看到了Carl发来的短信 “老鼠” 然后他打电话来训斥我并威胁要杀了我的家人。
这不是一个 “他说,她说 ”的案件。他的所作所为有清晰的照片和视频证据。
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非常害怕。我担心如果我让警察进去,Carl会有多生气。我担心他会对我的家人下手,所以我没有打开前门。与此同时,警察以为Carl还在房子里,所以他们最后叫来了战术小队。
最后,他们出现在房子的侧门,那里的摄像头没有麦克风。在那里,我们协商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试图说服我开门。一想到Carl会追着大家来,我就害怕极了。最后,一个警察说,“你能把门打开一点吗?” 我慢慢地转动门把手,警察把靴子伸进门里,我开始大声尖叫:“他会伤害我们!他会杀了我们!离开这里,我会没事的!” 很显然,我并没有没事。
就在这时,由男性警官组成的战术小组像追捕犯人一样冲进门来。他们从上到下搜查了整个房子,寻找Carl的踪迹。他们搬来梯子,爬上阁楼。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还有阁楼。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他们没有任何技巧,也没有考虑到我的处境。他们派了一名男性医护人员来检查我的情况。我浑身是血,不停地尖叫,根本不允许一个男人靠近我,所以我拒绝接受治疗。医护人员坚持要我去医院,但我还是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他们派来的是个女的。
整个警方互动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他们对Carl发出了逮捕令,罪名有三项:殴打他人造成身体伤害、持械伤人和发出死亡威胁。警察说他们会在外面停一辆巡逻车过夜几天。他们还签发了限制令,这意味着Carl不能回他家。因为那是我的主要住所,但我不能呆在那里,我需要找个地方去。我骗了所有人,说我要去一个女朋友家。但我没有去。我给Carl发短信,问他在哪里。他给我发了一个家庭聚会的地址。我的想法是,如果他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就会更安全--我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如果周围有朋友,他可能就不会打我了。我尽量多穿几件衣服,遮住身上的伤痕,然后去找他。他没有道歉。他表现得一切如常。派对上的人们都看着我 他们看到了我的黑眼圈。他们知道,但没人说什么。
我们走后,Carl躲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家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整个经历所带来的肾上腺素终于消退了。我走进客房,躺在那里,头怦怦直跳。我记得我摸了摸鼻子,摸了摸全身的伤口,摸了摸头。我到处都在流血。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想。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受伤了。我站起来,自己开车去了阳光布鲁克医院。
到了医院,我告诉工作人员我的男朋友打了我,他们把我安置在一间单人病房,并叫来了一名警官。他们给我做了全身 CAT 扫描。奇迹出现了,我没有骨折。但我有脑震荡,脑部肿胀。警官问我Carl在哪里,我撒谎说不知道。他曾威胁要杀了我的家人,现在还在逃。我不想让他更加生气。在那些时刻,我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我受到虐待和强制控制的影响。我仍然处于震惊状态,无法做出理智的决定。
那天晚上我出院后,回到家取了一些衣物,但我还没准备好告诉别人关于虐待的事。我仍然需要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住进了一家酒店。那时,我爸爸给我发了短信,问我Carl是否伤害了我。我撒了谎,说他没有,只是我需要休息。四天后,Carl终于自首了。他被关了一夜,之后以500元的保释金获释。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回家。我担心狗狗和尼古拉斯,所有的物品都在那儿。我仍然对那个地方有依赖感。到这个时候我已经非常累了,仍然无法做出清晰的决定。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觉得Carl控制着我。所以,星期二早上,当Carl从监狱出来时,我从酒店退房,请他来接我。我注意到他有个黑眼圈,但当时我无法理解。我不记得打过他。我后来才知道,在逃亡期间,他让一个朋友打了他一拳,试图让人看起来是他为了自卫才打了我,但警方并不相信这个说法。
我感觉自己像个空壳一样在四处游荡。星期三晚上,我感到剧痛,但Carl还是试图与我发生性关系。他说他需要。我告诉他我身体上无法和他发生关系,我全身都很疼。他对我拒绝的回应是拿出手机,给我看一系列 Instagram 上的女性。他翻看她们的资料,说:“她比你性感,她比你性感。”他告诉我,如果我不能提供性,他会去找别人。
逃离魔窟
那是我的崩溃点 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和Carl在一起,我就会死。过去几个月的动荡和混乱终于降临了。我想睡觉,但睡不着。我太痛苦了。
我知道我需要告诉家人,但我太害怕了。第二天,趁卡尔不在,我买了一箱伏特加苏打水,来到地下室的影剧院,灌了三瓶,终于哭了起来。首先,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兄弟,告诉他我有麻烦了。然后,我去了一个朋友家过夜。第二天早上,我哥哥请求我允许他告诉我父母,我父母马上来接我。我当时歇斯底里。我只带了钱包和护照,其他什么都没带。我们驱车前往 90 分钟车程外的父母家。我又哭又闹,头上已经结痂的伤口又裂开了,结果又被送进了医院。
在父母的帮助下,我向警方提交了一份正式声明,警方因此又对卡尔提出了两项指控:暴力威胁恐吓和试图通过劝阻证人妨碍司法公正。当时我父母的房子正在装修,房子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切都乱成一团。我知道我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担心我住在哥哥家,因为他的女朋友和他住在一起,卡尔知道地址。所以,在父母家住了几天后,我去了密西沙加的一个好朋友家。
八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回到城里,在约克维尔与一位朋友共进午餐时,看到卡尔缓缓驶过。我感觉他在跟踪我。我知道我需要离开多伦多。最困难的是离开尼古拉斯。我没能和他道别。袭击发生后的一两个星期里,他给我发短信,说 “我爱你 ”和 “晚安”。从 2021 年 8 月中旬起,我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这让我每天都心碎不已。
我在阿尔伯塔省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看望我的兄弟。我还去加州看望了一些朋友,在那里我终于有了安全感。就在那时,我决定开始办理搬到洛杉矶的手续。2021 年 11 月,我终于拿到了签证。在机票、签证、公寓定金、买新车和搬家等费用之间,我花了 6 万美元。我认识到,能够负担得起这笔费用是我的荣幸。大多数幸存者都负担不起。
将施暴者告上法庭
在父母的帮助下,我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200 万元。我应该为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得到赔偿。我要求赔偿人身伤害、收入和工作损失、疼痛和痛苦、损害赔偿以及心理创伤。卡尔在辩护词中否认袭击我,并声称我的伤是自己造成的。
与此同时,我在等待卡尔的刑事审判日期。这不是一个 “他说,她说 ”的案子--他的所作所为有清晰的照片和视频证据。我想他会被定罪,然后进监狱。不可能有其他结果。但我知道,Covid 造成了法院系统的延误,导致更多的指控被搁置。我母亲和我以前的邻居都给我转发了他们读到的关于约旦裁决及其持续影响的文章。我很担心,如果卡尔的庭审不能尽快安排好的话,它就会发挥作用。但我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2022 年 2 月,负责刑事案件的警官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我,审判定于 2023 年 2 月进行。这样的时间安排违反了乔丹案的上限,即一个月左右。我在回复中引用了 R v. Jordan 一案,告诉他们需要重新安排时间。后来,这位警官在电话中说,法院绝不会中止像他这样的指控。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案子。没有这种可能。
几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了自己录下的一些关于卡尔虐待我的旧录音。我还有一些瘀伤的照片,于是我把这些都拿给了主管警官,作为卡尔所作所为的进一步证据。由于卡尔在历史上对我进行过辱骂,因此控方在联邦一级又提出了三项人身伤害罪的指控。
202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我正在洛杉矶拍摄一个项目,这时我接到了受害者服务部的电话,告诉我所有省级指控都已中止。我将不再接受审判。他们说,我应该试着忘掉一切。我感觉我的生活被彻底击垮了。他们曾向我保证这不会发生,但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说是Covid造成了延误 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让他们重新安排庭审时间,但他们说无能为力。我给警察局和受害者服务部打了五天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检察官。关于我的案件,他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就好像他从未打开过档案一样。他告诉我,他有 200 多个案件要处理。他说他会提出上诉,他也提出了上诉,但被驳回了。
我唯一的一丝希望就是卡尔能在联邦指控中被定罪。新的检察官被指派负责联邦案件,2023 年 5 月下旬,她向我保证,她会将案件审理到底。我还聘请了一名刑事律师帮忙。但是,2024 年 1 月 12 日,联邦检察官告诉我,她没有时间进行刑事审判。她说,与谋杀案相比,我的案子并不重要,所以她会用和平保释金来代替,这种保释金就像限制令一样,每次有效期为一年。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她毕恭毕敬,但听到这句话,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告诉检察官,她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如果卡尔杀了人,她的双手就会沾满鲜血。
和平保释听证会定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举行。我自己掏钱买机票,耽误了几天的工作,回到多伦多,在那里我宣读了一份长达五页的声明,详细陈述了卡尔对我所做的一切。他当时就在法庭上,我的心跳得很快,差点连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看着旁听席上的家人和前来支持我的 30 位朋友,我找到了力量。和平保证书获得了批准,但我必须每年自费回去续签。
我无法接受加拿大司法系统在看到这个故事和所有这些证据后,最终却对其束手无策。我开始给政界人士发邮件,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众议院议长泰德-阿诺特(Ted Arnott)从我小时候起就是我的家庭朋友。他表示愿意支持我。多伦多中心区的国会议员克里斯汀-黄-谭(Kristyn Wong-Tam)是另一个了不起的支持者。该法案将宣布亲密伴侣暴力在安大略省是一种流行病,承认幸存者的痛苦,并允许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危机。当我在多伦多参加和平债券听证会时,Wong-Tam 邀请我参加有关该法案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进行得很顺利。在媒体宣布后的两周内,我们得到了全省的一致支持,将该法案提交二读,但它需要在省议会通过三票才能成为法律,令人失望的是,国会议员投票不支持将其提交三读。我们还在努力修改保护幸存者的法律,如《刑法典》第278条,该条允许施暴者获取受害者的医疗记录。我们还在努力支持第392号法案,该法案建议检察官可以为R.诉乔丹案的例外情况进行辩护,并允许卡尔的案件提交法庭审理。

自从我公开自己的故事以来,已经有数千名幸存者在社交媒体上或私下与我联系,分享她们的经历。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故事: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没有任何资源或支持,不知道该找谁,也没有人指导她们如何恢复和伸张正义。这促使我创办了 EVE:End Violence Everywhere。这是一个基于我在面对虐待时的愿望而建立的组织,它提供端到端的服务,培训倡导者帮助幸存者浏览法律系统、联系律师并寻求治疗。它就像一个一站式商店,可以为幸存者提供所需的所有服务。在美国,每个面临亲密伴侣暴力的人都会得到一名非政府倡导者的帮助,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计划。加拿大的受害者服务人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他们训练不足,工作过度。由于案件量大,人员流动率很高。在 EVE,我们确保倡导者能够为受害者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知情的、富有同情心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 EVE 的服务帮助了 20 多人,我希望能壮大倡导者团队,从而帮助更多的人。
我已经尽我所能,将我的创伤和挫败感转化为行动。去年 10 月,我在加拿大艺术与时尚奖颁奖典礼上发言,与业界领袖分享我们的宣传工作。作为 “反暴力之声”(Voices Against Violence)活动的一部分,我还在女王公园(Queen's Park)外领导了一次集会。“反暴力之声 ”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联盟,致力于消除加拿大的暴力行为,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这是当天在全国各省立法机构大楼外举行的 12 场集会之一,旨在提高人们对亲密伴侣暴力的认识。
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杀戮女性事件持续上升。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有 850 名妇女被杀害,这意味着每 48 小时就有一人死亡。而在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男性嫌疑人杀害妇女和女童的案件增加了 27%。因此,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我的疗伤工作也在继续。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接受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写日记和内部处理,才能够如此坦诚地谈论我的案件和施虐者。
我仍然在洛杉矶工作。我相信,这就是我还活着的原因,我回到多伦多时从来没有安全感。我坚信,只要卡尔还逍遥法外,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2022 年,一个女人在 Instagram 上联系了我。她说她和卡尔交往了大约七个月 她想为我起诉卡尔的案子提供帮助 但没过多久 她就从Instagram上消失了 之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我会继续回到多伦多,至少每年一次,重续我的和平纽带,继续我的宣传工作。加拿大曾经是我的家,但现在却是我差点丧命的地方,也是施虐者逍遥法外的地方。我非常想念多伦多的朋友和家人,但回到这里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在这里时会过度警惕。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卡尔因为他对我所做的一切而入狱,同时改革司法系统,让其他暴力幸存者不必经历我所面对的一切。
来源:toronto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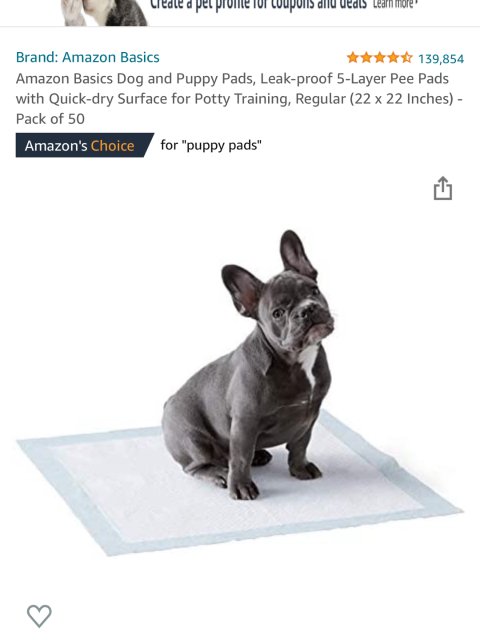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1
:这法官居然没被拉下来